
文|林培源
《登春台》和格非的前作《月落荒寺》《隐身衣》一道,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“拼图式”小说三部曲——所谓的“拼图式”不过是临时说法,这是因为《隐身衣》和《月落荒寺》互为“阴阳面”,后者系前者故事的“前传”,而《月落荒寺》主人公林宜生在《登春台》里只是一闪而过,后面两部在故事的依存关系上相对较弱,但三部作品之间精神的内在勾连,仍为当代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叙述范式。
报告期内,随着各地区域政策的变化,影响生产进度不利的政策因素减少,我公司项目生产进度加快,验收进度较去年同期有所好转,进而营业收入增加,毛利增加,从而净利润增加。我公司产品是客户重要的生产性装备,并非日常原材料。公司客户通常在研发、生产新车型或升级改造原有车型时,采购相应的智能装备系统。由于客户新车型分布不均匀,生产周期长短不一,采购的产品类型、金额存在波动,且客户采购的智能装备系统由于产品设计、整体规模、技术要求差异较大,终验收时间分布不均匀,因此我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存在波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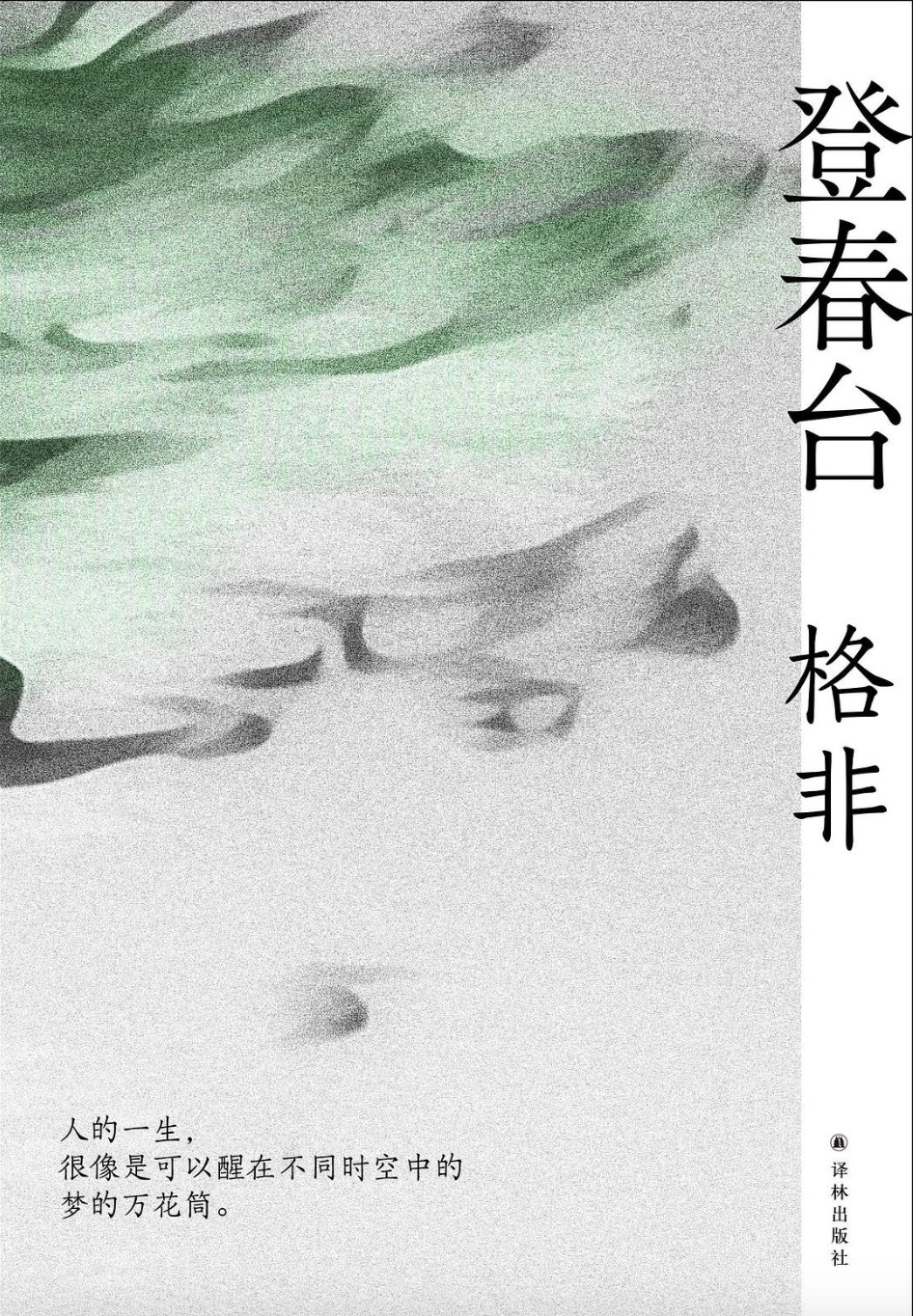
《登春台》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2024年3月
有别于《隐身衣》《月落荒寺》,《登春台》写到的人物并无主角、配角之分,小说主体的四个章节类乎四段人物小传,以一种交叠、重合的方式融为一体。在人物关系上,周振暇系“神州联合科技公司”的前董事长,沈辛夷、陈克明、窦宝庆是这家主营公路运输的物联网公司员工。小说讲述的便是四人在“春台路67号”(神州联合科技公司所在地)命运交汇的过程,此即“登春台”的实指。进一步联想,“登春台”语出《老子》“众人熙熙,如享太牢,如登春台”(唐人陆贽亦作有《登春台赋》),以之为名,自有虚指和深意。
近年来,格非“重返传统”的倾向已经得到学界和读者公认。此处所谓的“传统”,不仅囊括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等古典叙事,还包括以狄更斯、巴尔扎克等为代表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。格非曾评价道:“我们在阅读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的时候,作品中的‘我’虽然不能等同于狄更斯,但读者通过‘我’(叙事者)的语调和立场来揣摩辨认作者(狄更斯)的声音,可以十分方便地与作者建立起某种同盟关系,从而完成在阅读中十分重要的价值认同。”
狄更斯的第一人称小说和普鲁斯特的“匿名”叙述者一样,都能引领读者进入故事、与作者“建立起某种同谋关系”。比如,格非《望春风》的第一人称就有助于传递价值认同、沟通读者的情感。此外,这部小说里频频出现的叙事交流也和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异曲同工。当然,传统话本和“拟话本”小说也不乏“诸位看官”“欲知后事如何”等说书套话,它们旨在仿拟“说书”的叙事交流、营造“现场感”。《望春风》借鉴转化的正是上述两个传统——无独有偶,《登春台》里也存在明显的叙事交流。
在格非这里,重返传统并非机械地沿袭,而是经过现代主义洗礼之后有所选择和舍弃,从而造就一种复合的、再造式的现实主义。《登春台》拥有19世纪以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特征——以线性时间为主讲述故事、以刻画人物形象的敷设情节,这种写法在单独章节里表现得较为彻底。举例来说,“沈辛夷”一章就沿时间顺序依次讲述“90后”女生沈辛夷的出生、成长,和母亲贾连芳的紧张关系,初中春游时受人猥亵患上抑郁症,以及成年后到北京求学、与桑钦相恋,硕士毕业后进入神州联合工作等一系列故事,映入读者眼帘的是一位敏感、孤独的女性形象。从这点看,沈辛夷和《月落荒寺》的楚云在精神气质上相似,二者共享一种“楚云易散,覆水难收”的凄苦命运。
《登春台》四位人物都是从乡村世界的秩序中“脱嵌”出来的:沈辛夷命运的转折发生在读初二那年,春游时她不幸遭人猥亵,后来患上抑郁症,加上与母亲关系的恶化,她无时不想逃离家乡。抑郁症发作的那些无助时刻,沈辛夷意识到“在无情的时间及其那原本咬合得十分紧密的齿轮的转动中,唯有她一个人不幸被抛了出来”。“时间”在此别有深意,它指向寻常生活的秩序,“被抛出来”意味沈辛夷从由家庭、血缘关系和村庄等组成的乡土秩序里“脱嵌”了;陈克明和村庄的关系则随中国加入WTO、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和奥运会的举办、北京的城市化进程而动摇——不管是在后厂村一带向租房的务工者收取保护费,还是接管发小刘昆吾的服装厂,抑或是从事建筑和装修行业、跑出租车,自称“乡巴佬”的陈克明始终和北京这座城市唇齿相依;窦宝庆因为手刃侵犯姐姐的羊贩子、掩埋了尸体,才借着外出打工的名义逃至北京;周振遐对故乡的记忆最为短暂:“关于故乡长达七年的记忆,最终被压缩在了这样一个场景中:他拎着两条‘翘嘴白’去竹林寺看望师傅的途中,遇到了猝然而降的一场春雨。他在一座废弃的砖窑中避雨,随后做了一个梦。”
相较于《月落荒寺》,存在与虚无、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以及“人应该如何生活”等哲学问题的探讨在《登春台》得到了更加生动的“赋形”,与人物命运产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。比如沈辛夷在少女时期就时常觉得“自己不是生活在现实中,而是活在那些由言论、训诫、箴劝、格言、琐谈、意见、聒噪等声音的碎片所围困的黑暗之海上”。春游时被猥亵后,沈辛夷骤然发现世界变得陌生而不可理解。命运的不可知、灾难的突然降临,令她从训诫、箴劝等话语组成的世界一头栽进了“真正的生活”。她的抑郁症,成年后和桑钦无疾而终的恋情,乃至长期以来与母亲别扭的亲子关系,都是“真正的生活”不可或缺的部分,只有体验了“真正的生活”,沈辛夷才能完成其成长。
不管是写景造物,还是叙事抒情都别有韵致,《登春台》都为小说发挥其“道德想象力”提供了巧妙而恰切的媒介——不管是《北方法制报》的记者小罗据窦宝庆经历所写的文章,还是窦宝庆假托他人口吻对郑元春讲述其行凶过程的情节,都暗合努斯鲍姆说的,“文学扩展了我们的经验”。也就是说,只有借助想象和虚构,才能更好地让读者与作者建立起情感的共鸣与精神联结,讲述对“人应该如何生活”的看法。
本雅明有言,故事总是或明或暗地蕴含着某些实用的东西,“无论哪种情形,讲故事者是一个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”。“实用的东西”当然也包括道德教训,《登春台》对人性善恶的书写,尤以窦宝庆为显著例子:因对郑元春透露了杀人的经过,窦宝庆最终被逮捕。在被押往响水洞监狱的途中,他终于领悟到,母亲的发疯多半和他的行径有关,父亲将其打发到北京去,是希望儿子能“从此远走高飞,从一个世界,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,生活就此翻开新的一页”。以此为例是想说明,经验的讲述、转述甚至伪造和捏造,反过来又彰显了人性的幽暗复杂。文学(形式)和哲学(内容)在此交相辉映,成为一曲不折不扣的“双重奏”,这也是《登春台》作为一部书写当代中国人精神史、生活史的小说的意义所在。
(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“云山青年学者”)两融和杠杆